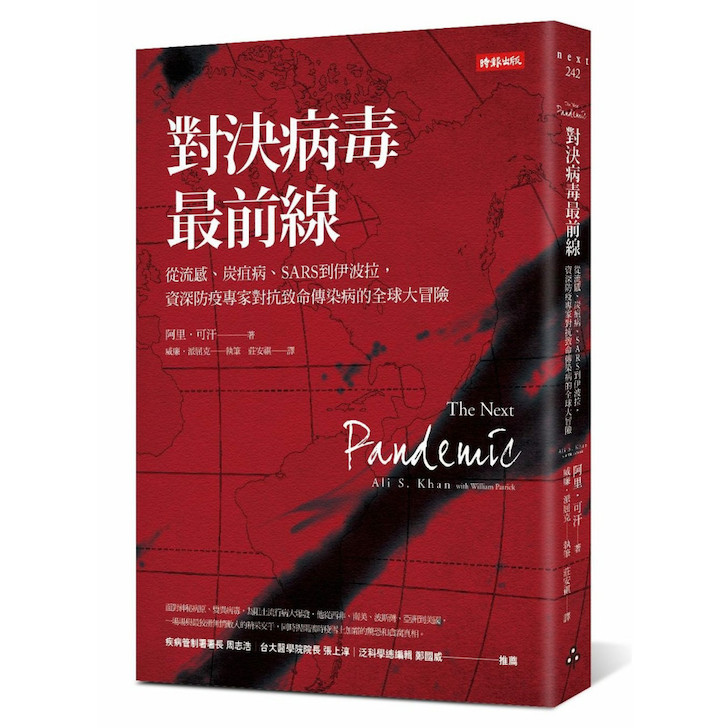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接種季,過去我甚少理會,因為要自費去打疫苗,一來嫌麻煩,二來要花小朋友。不過去年十月開始,我就乖乖去打流感疫苗了,一整年都不必擔心在上課或開會時,身邊的人很虛弱地告知得了流感,再也不需要活在恐懼當中,還能老神在在,一整年都沒得流感,所以現在都勸朋友也要去打流感疫苗。
會想到要打流感疫苗,是因為去年初實在太慘了,得了一次普通感冒,後遺症拖了一個多月,才剛痊癒,又得了另一次A型流感,把我搞得極為虛弱,在家躺了兩天休息,病情還是一直加重,在全身虛脫且非常痠痛的情況自行就醫,差點暈倒在路上。
勉強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到診所,做完快篩時原本得走到候診室等個十幾分鐘,沒想到腳一踏出診間,醫生馬上叫回,還拿著快篩棒說「滿格耶!」。雖然服用了克流感,三天後就顯著好轉,可是那次的經驗實在太痛苦了,於是我決定年年都要打流感疫苗,也奉勸各位也去打疫苗。
2008到2009年,美國除了被金融海嘯搞得翻天覆地,最早稱作「豬流感」的H1N1流感病毒也讓很多人發燒,包括我。過去俗稱西班牙流感的疫情爆發時,曾造成上千萬青壯年族群死亡,現在的流感多幾個突變也可能會頗可怕,更甭提還有跨物種的感染,例如從鳥類或豬隻跳到人類的。
常見的流感都能把人搞得七葷八素了,更甭提其他更恐怖的病毒。SARS肆虐台灣時,我正在唸碩二。我現在的身材和當時相比,大概胖了近二十公斤。SARS在台灣造成嚴重恐慌時,我的體重就在兩個月內爆增十公斤,真的都是SARS害的。
不是因為我得了SARS會爆胖,雖然當時我因感冒輕微發燒,差點就要被通報。而是因為SARS期間,學校游泳池關閉了好幾個月,直到我碩士班畢業都未開放,讓我無法運動而爆胖。當然,這和那些在疫情最嚴重期間喪失親友的人相比,實在不值得一提;近年,我們也見識到如伊波拉和茲卡分別在非洲和美洲造成的悲劇。在有如世界末日的疫情失控時,第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和科學家究竟怎麼面對來未知的病毒和病菌?
防疫資歷超過二十五年的阿里.可汗(Ali S. Khan)醫師長期在公共衛生領域擔任第一先遣部隊,是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公共衛生準備暨應變前主任,現在是內布拉斯加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他出身入死地潛入各種危險場所,直接面對危險病毒和病菌,所到之處遍及非洲、南美、波斯灣、亞洲和美國,處理過的危險傳染病有漢他病毒、伊波拉、禽流感、猴痘、炭疽病、生物恐攻、鼠疫、西尼羅病毒、裂谷熱、SARS、卡崔娜颶風、幾內亞龍線蟲等等。
他和作家威廉.派屈克(William Patrick)把多項冒險故事寫成《對決病毒最前線:從流感、炭疽病、SARS到伊波拉,資深防疫專家對抗致命傳染病的全球大冒險》(The Next Pandemic),很精彩地為第一線的勇敢醫護人員和科學家作了第一手的報導,講述他們如何在有限的資訊下,分秒必爭地做出重大決策以保他人及自身安全,並且試圖逆轉疫情。
可汗在《對決病毒最前線》談到:為什麼我們會不斷聽到新傳染病排山倒海而來?在旅行比過去便宜和方便許多的今天,旅客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身體當作病毒培養基長途運送病原。許多病毒藏在如蜱、嚙齒動物、蚊子、蝙蝠、猴、駱駝等等其他動物體內,有些因為環境的破壞或者不當的接觸而傳染到人體,然後無心地在人群中散播。
亞洲幾個國家爆發SARS疫情時,台灣被搞得人心惶惶,一些決策錯誤造成社會中的人際信任受到衝擊,對經濟也有沉重的打擊。當時,可汗趕赴香港和新加坡勞碌奔波地協助控制疫情。各地公共衛生官員奮力對抗SARS的故事,還被大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拍成大受好評的超寫實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
新興傳染病的病原故然可怕,可是人類可能更可怕──病毒和病菌會被有心人當作恐怖攻擊的武器,例如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談論的華盛頓國會山莊炭疽病攻擊,和犯罪偵探小說一樣驚險萬分。
還有,在四處對抗病毒的奔波勞碌中,可汗也見識到了許多政治和結構性問題,使官僚機構疏忽防疫工作,輕則互踢皮球,重則甚至在社會發生慘烈狀況時還趁火打劫、撈取政治利益和錢財。2005年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就是這場人禍的最慘痛教訓。在世界第一超級強權中,一場颶風是照妖鏡,讓世人慘痛地見識到在美國當窮人是會有多悲劇。不過,可汗指出,這一切悲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和致命病毒及病菌大對決,已經讓人心驚膽顫,不幸的是,近年還有假新聞來亂,有心人散播疫苗有疑慮的假新聞,不知情的人還製作成長輩圖以為是在幫助朋友,哄騙民眾拒絕為孩子打疫苗,讓更多不幸的老弱病殘在疫情中更脆弱。
無知和恐慌,讓疫情雪上加霜,第一線的科學家和醫護人員也會感受到恐懼,他們勇敢地冒死工作,是犠性小我完成大我的偉大情操,我們能活在免於恐懼當中,真的要好好地感激他們!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對決病毒全境擴散最前線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獨裁者手冊


香港原本是個講法治的文明城市,可是在特區政府一再傲慢蠻橫,香港警察不斷公然違法地連記者和旁觀者也不放過地施暴,現在大學校園都淪陷,還對大學校長、校董直接施行暴力,更甭提殺害、輪姦抗議者,法治精神蕩然無存。讓全世界眼睜睜見識到什麼叫做獨裁者的霸道!
原本大部分自由民主的國家,十幾年前樂觀地以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網路科技,能夠讓既不中華,也非人民,更非共和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專制極權國家走向民主法治,或者至少愈來愈開明開放,所以才擁抱中國更積極地參與全球的經濟發展中。沒想到,嚐到經濟甜頭的中共權貴,卻更加把權力一把捉在手中不放,並且利用各種科技來監控人民,生怕中共政權的不合法性被發現,對內對外都不斷輸出假新聞,還有試圖左右其他國家的選舉,利用大部分自由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來破壞民主法治精神。
因為專制獨裁技術的輸出,試圖左右其他國家的政局,中共已確定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世界公敵!任何享受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公民,對要警惕這股暗黑獨裁勢力對我們珍惜的普世價值的侵蝕!
面對這個獨裁巨人,我們該如何是好?來讀讀這本好書《獨裁者手冊: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為什麼國家、公司領導者的「壞行為」永遠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認清獨裁者的真面目吧!
《獨裁者手冊》的分析極為獨到,除了國家政治,甚至連公司、球隊的治理都討論到,也可視作是企業管理的必讀好書!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本書讓我們對江湖有更高的洞見!不管是在國家還是組織中,只要當上領導人,無不想擴權和延續自己的統治,忘了自己僅是暫時受委託來管理國家或組織,以為國家或組織是自己私用的囊中之物。
《獨裁者手冊》作者布魯斯・梅斯吉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艾雷斯德・史密斯(Alastair Smith)長期研究權力的遊戲規則,把多年的學術研究心得總結在這本好書中!政治上的算計和企業中的明爭暗鬥,本來就是一場場精彩的大戲,這本書讀起來毫不枯燥!
《獨裁者手冊》當頭棒喝地指出,統治者位子坐得穩不穩,和他的治理的良窳無關,而是他怎麼收買盟友!要讓一大群人聽命於極少數人,是不容易的,但只要掌握著對的方法,就能奪權!而且還牢靠地在大位上胡搞瞎搞!這個觀點可能很令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像是憤世嫉俗,可是其實才是政壇上的真相,也只有認清了真相,我們才能改變世界。
所有領導人,目標不外是要獲得權力,然後保住權力。要坐穩大位地獨裁,要認清創造權力的三個基本群體:廣大人民、重要成員、關鍵核心群,讓關鍵核心群的人數越少越好,並且切忌讓任何支持者擁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讓他們有被換掉的危機感才會一直忠心耿耿。要找到利益、控制利益、分配利益,而且絕對不要把利益從支持者手上拿開,讓人民過著苦生活是沒關係的!這就是為何獨裁者必定會貪腐地魚肉鄉里!
當然,生活在自由民主世界的公民大可唾棄不折不扣的獨裁者,可是難怪民主制度就不會有獨裁者了嗎?《獨裁者手冊》也讓我們認識到民主制度的不完美。在民主國家,領導人也要打賞支持人,也要分封關鍵核心群為諸侯,在選區中大撒幣。政客才不關心何謂「國家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
算不算得上是獨裁與否,盟友圈的大小是關鍵,如果盟友人數愈少,其政府就愈容易被收買。要收買民主國家的難度遠高過收買獨裁國家。這也是為何美國遇到地緣政治上不如自己利益的非洲或中東民主國家,就暗中扶持聽話的獨裁者。
生活在獨裁專制國家,就是抽到人生的下下籤!儘管在《獨裁者手冊》中,民主也好、獨裁也好,差別僅是要收買的人數多寡,可是很明顯的,如果有選擇的狀況下,人民還是會選擇民主自由的國家,因為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廣大的群眾都是政客競相取悅的對象,當然比在獨裁國家中,看領導吃肉、自已喝湯,甚至連施捨來的湯能不能一直喝都不確定,還爽太多了!連中共的高官和權貴也不例外,他們大量重金把小孩送往民主自由的歐美國家,就連現任領導維尼熊也有一大堆親戚移民歐美各國。
那些標榜自己愛國,在大陸高舉反美大旗,動不動就在公眾場合對美國口誅筆伐的「反美鬥士」,卻把自己、親屬、財產都轉移到美國去了。中共高級五毛司馬南就曾說過:「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他們移民或留學了歐美,仍享受當地的言論自由和人權批評民主自由和當地政府,噁心到嫑嫑。
很多人以為專制國家更有效率,也有不少人被專制國家的洗腦給騙著了,以為專制國家的軍隊會更強,可是《獨裁者手冊》舉了實例,並且邏輯論證地指出,專制國家的軍隊往往是為了維護少數人利益而存在的,保家衛國反道是其次。戰爭的勝敗,對民主領袖來說是更值得在意的,民主國家對戰爭也更全力以赴!
獨裁者難道就一定能掌權到千秋萬世嗎?《獨裁者手冊》指出,當統治者病危時,無法再保證盟友的利益,或者免費的外援被抽走(外援往往只會造福獨裁者),那就是統治集團出亂子的時候。因為群眾抗爭而真正動搖獨裁者的情況,很不幸的,真的很少,那些因為示威抗議而下台的獨裁者,往往也是因為抓襟見肘而無法收買軍警及盟友的。
這麼說可能很殘忍,可是與其在街上和黑警逞凶鬥狠,還不如好好讀讀《獨裁者手冊》等等好書。就像時政評論家鄧聿文在《紐約時報》中文網觀點與評論版說的:「不管外界和中國人喜不喜歡,黨國體系的升級版已經鑄就。這個被一些人稱作『完美極權』的體系目前看來牢不可破。我不清楚如何破解它,但任何完美極權總有脆弱的一環。」
是的,任何完美極權必定要脆弱的一環!那我們必然能夠擴大聯盟人數,讓上位者不得不收斂,最終還政於民!

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每個阿宅的短歷史



基因,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你想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事情。現在歐美也有頗多基因分析服務(像是23andMe),你只要用一根棉花棒抹些口腔黏膜細胞,密封在管子寄過去,他們就會給你一份報告,讓你知道以後的健康會有什麼下場等等。除了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我有位韓裔美國教授朋友,還意外發現因韓戰而失散多年的表親,在美國團了圓。
2001年,我大學畢業那年,「人類基因體(基因組)計畫」完成了初步的草圖,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和英國首相布萊爾,率領英美科學團隊共同宣布成果。時至今日已過去18年,當時數千位科學家用了十年、花費上百億美元才辛苦完成的工作,現在幾個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花個幾十萬台幣,大概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完成。這樣的工作在我小小的實驗室也是家常便飯。
有趣的是,我們當時就在想,要把一個人類的基因體給完整定序並且組裝,除了一堆技術和經費的問題要解決,另一大問題是:那一個基因體,要用誰的DNA來做?誰能夠代表全人類來提供這個關鍵DNA?不管那個參考基因體是來自誰的,鐵定無法代表人類的多樣性。於是,幾年後又推出了「千人基因體計畫」等等。到了今天,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取得自己的基因體序列,花的錢可能不會比買一台iPhone XS Max還多。
有了這些基因體資料,科學家開始可以更有效率地應用生物資訊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遺傳疾病,並且為世界各地的人類尋根溯源,這也是為何我那位朋友能遠在他鄉找到失散的表親。基因體研究還能告訴我們多少呢?
《每個人的短歷史:人類基因的故事》(A BRIEF HISTORY OF EVERYONE WHO EVER LIVED: The Human Story Retold Through Our Genes)就敍述了用基因來追溯我們歷史的故事。作者亞當・拉塞福(Adam Rutherford)是遺傳學家,也是科學作家與廣播節目主持人,他在這本書中充當了歷史學家,為我們全人類的歷史解謎,告訴我們就現在最前沿科學所知,基因能告訴我們啥,還有無法告訴我們啥。
畢竟和語言文字相比,遺傳學的資料較不受政治迫害和文化同化等等因素干擾。《每個人的短歷史》告訴我們,在歷史上曾經活過超過千億位智人,即使如此,把我們每個人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往上追,沒出多少代,人類的數量就和你腸子裡的細菌差不多了,屆時地球除了人類也容不下其他哺乳動物。
事實上,如果這麼做,我們會發現原來絕大多數現生人類,可能是一小撮人的後代。畢竟很殘酷的,溫拿畢竟是少數,有關這一點,當我在課堂中提起,常常會有單身的情場魯蛇深切地說:「我懂......」貴族和王族有比平民高得不成比例的機會留下後代,所有我們的血緣一直往上追溯,很有可能就追到某朝的皇親國戚,實在也不該讓人意外。據說成吉思汗就留下了不少後代,說不定你我都和他有關。
拉塞福來自英國,也就是曾經的日不落帝國,現在的日沒落帝國,所以有不少故事是從英國人的視角來寫。因為你我都可能是王室後裔,他在《每個人的短歷史》詳述了英國王室的歷史,尤其是查理三世(1452-1485)那極為灑狗血的八卦:前幾年,他的骸骨出土,用DNA定序確定身分,也是很多歐美大報的頭版頭條新聞;但是他卻對用DNA揭露開膛手傑克身分的炒作嗤之以鼻,因為不嚴謹地用DNA做分析,恐怕和栽贓嫁禍差不多。
然而,拉塞福也非「純種」英國人,他也有印度人血統,小時候還因為同學稱他作「巴基」而痛扁人家。在書中他要告訴我們,過去我們對「某些種族先天會怎樣怎樣」的偏見,常常是以訛傳訛。非洲任意兩個部落的黑人之間的遺傳差異,可能都要比我們和白人間的還大。
人類也有比我們想像中更大的遷徙歷史。事實上,到異鄉探索,是我們人類的天性之一。我有位朋友,跟我一樣是馬來西亞華人,可是他卻長得很像混血兒,頗像西方人。我問他祖父母是從何而來,跟我一樣是來自福建泉州一帶。如果再早一些,我會懷疑是自己多想了,可是讀了些歷史書籍得知,泉州幾百年前曾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許多歐洲人和阿拉伯人,都在那裡留下後代子孫,就不足為奇了。
據說南方華人如果有絡腮鬍,就很有可能帶有阿拉伯人血統。而中國北方因為五胡亂華、還有宋朝時金國統治加上蒙古人征服時十室九空,大量遊牧民族移入北方,現在幾乎沒有所謂純種的漢人。而台灣的漢人,據說也有和原住民平埔人混血。
即使是最早倡導民族國家的歐洲各國,英國凱爾特人和統治一時的羅馬人留下來的子孫,以及後來征服的日耳曼人和入侵的維京人已混成了一鍋粥,而那些拉丁語系的國家就不說了,幾乎早就是歐盟,就連曾經提倡「血統純正」而把歐洲打得稀巴爛的德國人,在更早的過去歷經三十年宗教戰爭等戰亂後,也不算是純種雅利安人了。
事實上,最在意血統純不純正的,只有王室和貴族。《每個人的短歷史》提到,因為近親通婚,英國王室出現了瘋瘋癲癲的國王,曲折離奇的故事剛好可以用來玩權力的遊戲。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更慘,末代國王身體健康之差,就算在醫療發達的現代也沒能治癒多少,更甭提後來因為政治聯姻的通婚,把歐洲各國王室搞得血友病頻傳而玩殘,後來間接導致一戰的爆發。
現在基因體學的研究方興未艾,這算是大數據分析了吧,過去我們以為有了更多資料,就能夠清楚自己這個民族過去乾乾淨淨的歷史,沒想到太多戰亂、饑荒、瘟疫、遷徙等因素,已把很多地方的民族血緣打亂到連他們的媽媽都認不出來了。
全基因體學的研究,加上古DNA研究,對我們智人來說,最令人震撼的是:歐亞現代人類族群有2-4%的DNA來自尼安德塔人。這是來自《尋找失落的基因組:尼安德塔人與人類演化史的重建》(Neanderthal Man: In Search of Lost Genomes)作者帕波(Svante Pääbo)團隊的研究。


智人是大約二十萬年前自東非稀樹草原演化出來的,約十萬年前走出了非洲,在歐洲邂逅尼安德塔人,就和他們⋯⋯。帕波等人後來還趁勝追擊,定序了丹尼索瓦人的全基因體,發現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亞人和澳洲土著有6%的DNA來自丹尼索瓦人。這些發現,對人類演化研究投下一顆又一顆震撼彈,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描繪和思索人類演化的歷程。
其實,早有演化生物學家提出,尼安德塔人可能和我們的智人祖先混血,至少歐洲人可能帶有一部分尼安德塔人血統。這論點過去十幾年在學界吵翻天。曾經有一度,如果想看到人類演化生物學家翻臉,就在飯局上提這話題吧。我過去其實是對主張智人和尼安德塔人混過血的理論不屑的。
由於演化人類學及古生物學家對於現代人類起源以及與尼安德塔人的關係,一向頗多爭議,帕波的研究除了智力外,還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毅力,因為尼安德塔人粒線體DNA的定序結果剛出來,許多演化生物學家就先選邊站,不太相信那些結果,認為汙染的可能性太高。在這個課題上,他們要花比其他演化遺傳學的研究更多的力氣在排除汙染的可能性,才能得到一些榮耀。倘若不小心錯了,科學界的對手會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批判到無顏見江東父老。
帕波不斷試驗萃取絕種物種DNA的最新技術,努力排除古DNA汙染問題,建立可靠重建古DNA的黃金準則,憑著極大的決心和毅力把他們的研究推到頂峰,建立出來的SOP嚴格到雞蛋裡挑骨頭的地步,也拚出了極高的門檻,其他競爭者不易跨過。
前述那位韓裔美國教授朋友,甚至因為那個基因分析服務,連她帶有多少趴的尼安德塔人基因都知道。後續研究也發現了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智人等等之間有複雜的情欲流動,這種愛來愛去的劇碼,會隨更多資料的出現而愈來愈灑狗血。
現在,我們甚至能用尼安德塔人的基因體,回推他們的長相,甚至還知道他們的健康狀況。有趣的是,我們可能都受到來自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對健康的影響。近年還有研究顯示,藏族適應青康藏高原的稀薄空氣的基因,就很有可能是來自丹尼索瓦人。
我們人類大約有兩萬多個基因,遠比「人類基因體計畫」完成前,科學家預測的還少很多。基因,當然不是為了讓我們追溯自身的歷史而存在的,而是參與了我們的所有生化及生理功能,對我們的命運可能也有很大的掌控──我們常會聽說某個基因控制了某種人類性狀(例如乾濕耳垢),或者突變而導致某種遺傳疾病等等。過去,自信人類飽受遺傳控制的想法,誕生了「優生學」,始祖是達爾文(1809-1882)的表弟高爾頓(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
然而,這樣單基因產生的顯而易見表現型,其實是極少數,以致我們總愛用它們來說嘴。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的性狀都受很多基因控制,它們的效力甚至遠不如環境的影響重要。《每個人的短歷史》多次提到英國版的基因分析服務,也對他們有所嘲諷(例如,還能精確地把某人的出處追溯至某個村莊)。拉塞福警告我們,遺傳學是機率的科學,不是像物理學那麼精密(但是量子力學也有「測不準原理」啊),常常也非一翻兩瞪眼的。
是英雄所見略同吧,關於遺傳學的複雜性,羅伯.薩波斯基的《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也有很精彩的論述,指出我們的命運從來就甚少只受控於基因,基因提供了潛力和易受影響的程度。基因還會與環境有交互作用,環境對基因的調控至關緊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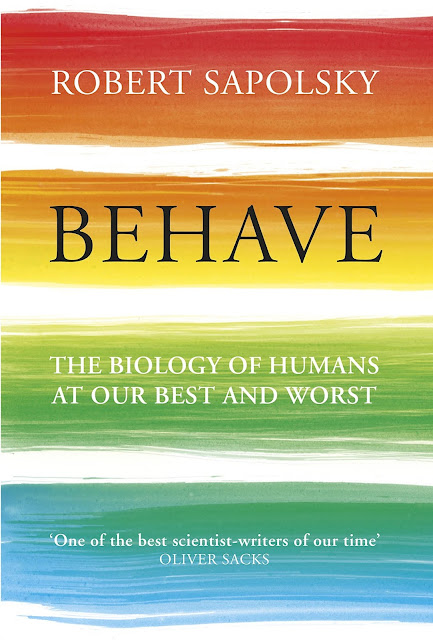
想要知道你自己的短歷史嗎?來讀讀這本趣味盎然的《每個人的短歷史》吧!
本文原刊登於博客來OKAPI閱讀生活誌
2019年11月1日 星期五
見龍在田


這二十年來大量的古生物學證據,愈來愈支持鳥類就是恐龍的學說。更精確的說,地表上一萬多種鳥類(包括田野的雞),都是鳥類恐龍。
因此,說恐龍早在6500多萬年前就滅絕了,可能錯得離譜!牠們不僅沒有斷子絕孫,後代還演化得非常快速,成了多樣性最高的羊膜動物,這在在體現了恐龍這類動物,不僅在陸地上稱霸的時間特別長久,也顯示了牠們演化上的潛力究竟有多大。
就因為牠們實在太成功,認識恐龍能夠讓我們了解過去的世界,以及今天的世界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古生物學家拉科瓦拉的這本《恐龍的啟示:為什麼了解恐龍,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Why Dinosaurs Matter)就是要帶我們穿越到恐龍主宰的世界去尋幽探祕。他主張,為了預測我們環境不確定的未來,研究過去的世界無比關鍵。
就像許多夢想投身科學研究工作的小孩一樣,我從小就對恐龍感到十分好奇。老實說,我的夢想之一,就是要複製出侏羅紀公園!這當然是項艱巨任務!雖然在小說和電影中,科學家似乎可以透過琥珀中蚊蟲吸飽的血液萃取到恐龍的DNA。姑且不論那些得到的應該是蚊子的基因,DNA分子的化學和物理性質幾乎不可能讓它們保存千萬年而無損。如此一來,我們終究無望了嗎?
別灰心喪氣!從這二十年來,古生物學提供我們的大量知識來判斷,這並非不可能,因為我們很清楚那些所謂的「恐龍」,應該用鳥類來還原,只要了解各種器官發育的調控機制,我們可以透過改造鳥類的基因體,使用現今最夯的基因編輯技術,一步一腳印地把一隻雞改造成像是一隻小迅猛龍,侏羅紀公園就不再是空想了!
為了達成這個終極目標,我們和許多實驗室仍要不懈地努力,以充分掌握脊椎動物器官發育及基因體學的知識!這些生命科學的知識對生醫工程等領域也非常重要!
恐龍會帶給我們智識上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戰,一起來共襄盛舉吧!
本文為《恐龍的啟示:為什麼了解恐龍,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Why Dinosaurs Matter)好評迴響
張貼者:
Gene Ng
於
上午11:48:00
0
意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