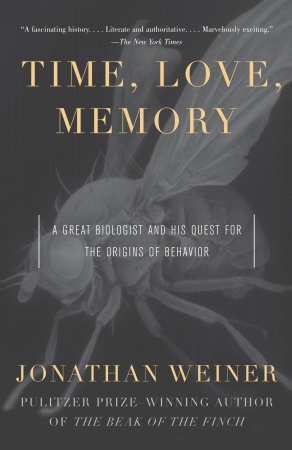
時間逝去無影,愛情只在回憶。
時間之苦短、愛情之甜密、回憶之凄美,叫人不勝唏噓。
言歸正傳,在這還是不要太感傷了。我可不是要在此道儘傷心往事,是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追尋時間、愛情、回憶之謎的故事。
故事主角Seymour Benzer及其科學王朝的傳記Time, Love, Memory: A Great Biologist and His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Behavior是科學作家Jonathan Weiner繼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得獎作品《雀喙之謎》(The Beak of the Finch: A Story of Evolution in Our Time)之後的一大力作,並榮獲國家書評圈?(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Weiner的《雀喙之謎》?述的也是非常重要但原本為大眾所不知的普林斯頓演化學家Rosemary和Peter Grant夫婦在加拉巴哥群島默默辛勞地研究達爾文雀的生態及演化,為演化學貢獻了極詳細的田野調查資料以佐證達爾文理論,長達廿幾年的感人故事。
Weiner是不可多得的科學作家,他的作品不僅深入淺出,他的文筆非常優美,唸起來有詩的味道。他的這部作品,注入了行為遺傳學一股生動活潑的生命力,並賦與了人文關懷。他也描述了早期分子生物學的萌芽──一個充滿瘋狂與熱情的時代啊。從他書中的軼事裡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有靈,可見科學最人性的一面。
Seymour Benzer,他可能對許多唸生命科學的莘莘學子來說相當的陌生。但卻他被作者Weiner譽為我們時代的無名英雄("one of the unsung heroes of our time.")。
而Time, Love, Memory表示的是什麼?是行為遺傳學研究的三大元素,也一位科學家對動物行為的遺傳學基礎的尋根究底之發現。時間Time是生理時鐘;愛情Love是性象;回憶Memory是學習與記憶。
Seymour Benzer的出身其實不是生物學家,他同DNA雙股螺旋發現者Francis Crick一樣是個「?落」的物理學家。他在四○年代協助電子學的開拓,但他卻迷上了生命的美妙,於是不務正業去和一群天才瘋子開創了分子生物學,對分子生物學的貢獻,他已堪稱大師。可是他厭倦了噬菌體的簡單,厭倦了出了一篇又篇描述枝枝節節的論文。他有了兩個女兒之後,非常好奇為何她們的格性為差異頗大,於是他決定去瞭解為何人類之間在著許多行為思想上的差異,瞭解我們的大腦到底在是如何運作底。於是他奮而往神經科學發展,他曾在因研究人類大腦半球分化而榮獲諾貝爾獎的神經科學大師Roger Sperry門下研學過神經生物學。但令人驚呀的是,他後來決定不搞正道去研究人類大腦(或高等生物大腦),他反而去玩些小不點的果蠅,連他母親都以為她兒子瘋了!正因為他出身物理學,所以他懷著一個信念就是要找尋行為的原子──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身為分子生物學家的Benzer堅信,就像許多性狀一樣,行為也必然有其遺傳學基礎。
Seymour Benzer在行為遺傳學(behavioral genetics)的開創性研究,不啻是一大革命!既然他偉大,那他拿了諾貝爾獎嗎?沒有,應該也不會有。因為他已經得過瑞典皇家科學院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科學領域所頒發的克拉福獎(Crafoord Prize)。那為何他仍漠漠無名呢?因為他不愛作秀,厭惡和記者打交道,也不愛寫書招搖,寧可躲在實驗室默默耕耘。這點和Grant夫婦很像,Weiner想必費了不少勁,用真誠打動他們接受訪問的。
Seymour Benzer和學生Ron Konopka在1971年利用突變果蠅的技術篩選到了第一個生理時鐘出問題的突變果蠅。正常果蠅通常會在淩晨時分或下午時分羽化,但Konopka發現他篩選到的第兩百管果蠅,可以在任何時候都羽化,他們終於找到了聖杯!該突變的基因period (per)是首次被發現的確確實實的動物生理時鐘基因,而且還有三個版本的突變:變長的per^l、變短的per^s和無規律的per^0。有趣的是,這些突變種都是Konopka在選擇兩百管果蠅內發現了,之後他們再也沒發現新的per突變了。於是立下了所謂的Konopka’s Law:如果你在兩百管果蠅內還未發現你要的突變種,那你就可以放棄啦。接下來Seymour Benzer等人還發現了另一個生理時鐘基因timeless (tim)。
而後來Konopka的故事卻也印正了學術界的嚴苛和無情。原本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可以讓他出人頭地,但他是個完美主義者,常不情願發表論文,因此在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界裡無法站得住。他被加州理工掃地出門後在一個小學院Clarkson教書,但最後卻連Clarkson的終身職都保不住。
隨後Seymour Benzer的實驗室仍有重大發現,他的博士後研究員Jeff Hall發現了影響果蠅交尾的基因fruitless (fru),fru基因突變的雄果蠅搞不清楚雌雄,可見一鏈突變雄果蠅排在一起「搞基」。在七○年代,性行為仍是個黑匣子,他們這個發現無謂是性行為的遺傳基礎之研究的一道曙光。影響性行為的基因其實還不只是fru,連per基因都對性行為有大影響。為什麼呢?因為雄果蠅在交尾前會振翅,是為一種情歌,而per的突變影響了其歌唱頻律。用荒腔走調去把美媚!?還能有戲可唱!?Hall後來到了Brandeis Univ.,他斷續研究per基因,他們利用正常per基因轉殖回復了果蠅正常時間感的實驗堪稱經典之作。
Seymour Benzer實驗室還有個大突破是利用果蠅來研究學習與記憶。有沒有搞錯!?用低等的果蠅來研究高等行為?連老狗都學不會新把戲了……但要知道,學術界嚴苛,可是自然界更殘酷!在自然界生存,動物必須懂得趨吉避兇,所以學會什麼是好東西,什麼東西最好一生再也不要再碰到,這是攸關存亡的呵。Seymour Benzer和另一位博士後研究員Chip Quinn發明了果蠅學習機──利用octanol或methylcyclohexanol來訓練果蠅的條件制約,用丟銅板的方式看看那個氣味是賞或是罰。基本上果蠅對octanol或methylcyclohexanol無特別偏好(Quinn為了找到適合的氣味來源,搞不好已經聞過全實驗室所有藥品的氣味了),因此當某氣味和?罰(電擊)聯結,果蠅就會避之唯恐不及。在學會趨吉避兇後,他們就可以在幾天後考考果蠅的學習效果。他們漂亮的實驗設計讓他們分離出一種單基因dnc突變造成怎麼都學不會新把戲的果蠅。爾後Quinn到了MIT,Quinn的學生Tim Tully到了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繼續對果蠅如何學習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要知道學習與記憶的研究可不只是單純象牙塔的故事,還可能是億萬黃金的。而吃威而鋼不過是男人的專利而已,健忘可是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之苦呵。他們的研究搞不好還可能導致出現「百忘解」什麼藥的。
然而和為名利而作研究的科學家不一樣的,Seymour Benzer對研究的熱情純粹是為了瞭解自然深藏的奧密。他的創意、遠見和勇氣開啟了行為學的遺傳學研究,他的徒子徒孫也把時間、愛情、回憶的研究發揚光大。他剛開始用來研究而被取笑的果蠅,不僅成為發育生物學家的寵兒(有趣的是,Thomas Hunt Morgan當初研究果蠅是為了發育學,但最後卻和學生Alfred Sturtevant搞成了遺傳學),也成了許多實驗室研究神經生物學的好材料。果蠅的研究也導致對人類的遺傳學之認識,也很少人能否認,果蠅的行為之遺傳學基礎和人類的是不一樣的。果蠅研究社群也是相當有趣的,無論是進行何種研究,他們都團結一致分享資訊和材料,而且分子生物學裡的許多新思潮就是在果蠅室繁複單調的篩突變、挑克隆時閒聊出來的。分子生物學開山始祖之一的大師Max Delbruck在同個時期也厭倦噬菌體後,也在加州理工轉而研究行為──真菌Phycomyces的趨光行為,但該真菌的遺傳可操作性不佳,結果就真的「老狗玩不出新把戲了」。
但Seymour Benzer開創了行為遺傳學的新學門之後呢?他對神經系統的偏好之後勝過了行為,他的第一任妻子Dotty過逝後,第二任妻子Carol Miller是南加大的神經病理學家。他們一起對神經遺傳學(neurogenetics)做出不少努力,但是他們對果蠅複眼發育的研究後來和柏克萊加大的Gerry Rubin相競爭,但卻顯然沒有後者成功。Benzer對行為遺傳學的出走,使得他的門徒Hall頗不能原諒他。Delbruck還為Benzer作了首詩來調侃他:
Physics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Genetics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Behavior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想對果蠅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有進一步瞭解,請參考:
Sokolowski, M. B. Drosophila: Genetics meets behaviour.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 879 – 890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