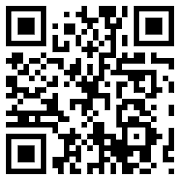從小時候讀了幾本給小阿宅的科學家傳記童書後,我就立志要當個科學家,並且天天把這個志向掛在嘴邊跟媽媽說。
儘管求學時也走了不少歪路,但究竟還真的投身科學研究的工作中。這樣的志向,在馬來西亞這個發展中國家,是相當特立獨行的,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物質生活都要很辛苦打拚取得,遑論花大錢去做不知有何用途的科學研究。即使到美國念博士班,為了不讓家人蒙羞,我都跟親友說是去「工作」。
即使是在富裕國家,社會大眾對於科學研究也感到陌生,科學家究竟在實驗室裡搞什麼鬼呢?真的是為全人類解決重要的問題,還是滿足少數人的好奇心?
我認識的大多數科學家,最喜愛的工作方式就是成天窩在研究室,厭惡社交生活,心無旁鶩、不見天日地埋頭苦幹。他們專心致志地力求搞清楚一個難解的謎題,廢寢忘食地整理閱讀文獻,絞盡腦汁設計實驗,孜孜不倦地重覆各種實驗,咬緊牙關地克服一再失敗的挫折。即使獲得不錯的成果,仍要兢兢業業地選擇發表的期刊,費盡心思回覆審稿者的問題甚至刁難等等,然後在出版論文後發現版權全都在期刊出版社手上……
甭說是一般社會大眾,就連我們的父母,甚至伴侶,都難以理解我們究竟為何而戰?走出實驗室外,我們與科學的距離真的是遙不可及嗎?
其實,科學始終來自人性!不管我們以為那些電影中,總是穿著白袍實驗衣的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看來有多麼高深莫測,就只是要回答我們對自然最最最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以及渴望解答的欲望。這些問題,不僅是我們小時候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時一直追問的,也是整個人類文明誕生以前,我們的祖先圍在篝火前就開始追究的。
過去,人類文明頗長的時間裡,對大自然好奇的探索,是不愁溫飽的有閒貴族或富人的專利。如果說火讓人類能演化出更耗能的大腦,那工業革命就讓我們能更有效地利用能源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們能夠在物質更豐沛的社會中,不愁吃穿地投入一定的資源,來滿足我們啟蒙的理性智識樂趣。
科學的方法也高效地讓我們可以跨地域、跨文化地再現重要的發現。也因為見識到科學的力量,當溫飽不再是大多數國民的問題後,後進現代化國家都無不爭先恐後地投入資源,強化科學研究的能力。而這些科研能力,對各國未來對抗氣候變遷和新興傳染疾病都很重要,COVID-19就讓我們見識到了寶貴的一課!
記得當年來台灣念大學時,剛躋身富裕國家的台灣也正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基礎研究上,經過了這二十幾年的努力,許多方面也漸漸和國際接軌,取得了不少豐盛的成果。有些當年可以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期刊論文,現在可能只能勉強用來升等而已。這些科學界努力奮鬥的成果,真的好到不能只有我們少數科學工作者知道,而應該成為全民的精神資產。
很幸運地,作為比大學更象牙塔的中央研究院,除了頂尖和傑出的研究,在科普方面也當了火車頭。感謝已故的中研院資訊所的天才研究員陳昇瑋博士的遠見和魄力,中研院成立了「研之有物」科普網站,請文筆生動流暢的小編們,為深居簡出卻努力地在各自領域推動科學進步的研究員們,寫下精彩的白話文報導和故事。
雖然歐美日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積極向社會大眾報導教授或研究員的重要及有趣科學發現,是行之有年的,但在台灣這無疑是科學報導的里程碑!我們不僅做出了國際級的研究,也和歐美日大專院校接軌重視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益!
更令人興奮的是,接續《研之有物:穿越古今!中研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時報出版將這些精彩絕倫的報導,集結成《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成為科普報導教科書等級的好書。
《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涵蓋生物、醫療藥物及生物工程三大面向,讓我們能窺見研究機構中不辭辛苦的生命科學家們,其實也可以有浪漫的科學情懷,用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排除萬難揭開科學謎題的謎底,同時也為人類健康福祉作出具體貢獻。
藉著《研之有物: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的各種研究,可以看見生命科學其實離我們的生活一點也不遠。這些知識一點也不冷冰冰,裡頭所有的科學故事,其實無時無刻發生在我們的周遭,只是我們可能視而不見,或尚未知曉箇中道理,這些科學故事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生活增添許多趣味。
這些生命科學研究,讓我們知曉了從細胞到個體再到整個生態系,各種生物是如何應對五花八門的問題,例如敵我的辨認、誘敵的陷阱、器官的再生、環境汙染的應對、族群的遷徙、能量的生產、養分的吸收、遺傳基因的重組、植物天然成份的防癌或抑癌、新藥的開發、飲食的營養與健康、大腦神經的退化、免疫系統導致的發炎、奈米疫苗的研發、全球傳染疾病的防治、永續能源的開發、個人遺傳資訊的應用、基因的剪接或編輯等等。
以上研究僅是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組各研究所傑出研究的冰山一角而已,相信不僅是中研院,台灣各大專院校也有許許多多精彩科學故事有待發掘和報導,相信這些科學發現真的不能只留在學術期刊的論文中,而是有必要成為全民的精神糧食,所以我們拭目以待,期望有更多精彩的科學發現被報導在科學網站或書籍當中吧!
本文原刊登關鍵評論

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研無不盡
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一個野心勃勃醫生的反疫苗戰爭



為了避免感染COVID-19之後的長期後遺症,我接種了三劑COVID-19疫苗,前兩劑是AZ腺病毒疫苗,第三劑是半劑量的莫德納RNA疫苗。
根據衛福部的報告,截至2022年6月24日,台灣接種兩劑COVID-19疫苗的人口比例已達82.98%,接種第三劑已達69.9%。可見有超過八成人口為了減少感染COVID-19的機會,願意承擔接種疫苗的不適副作用。完全接種後,還有近七成人口也願意再追加第三劑。然而,三不五時還是有人靠北疫苗接種是陰謀,指出還是有人接種三劑後病死。
姑且不論接種疫苗後病死的病患絕大多數本來就是不易產生免疫力的高齡、長期慢性病患(所以更應該接種更多劑疫苗),統計學也能告訴我們,單單從兩劑疫苗到三劑之間,能夠拯救多少性命。例如,6月27日公佈的資料中,死亡的127人中打滿三劑疫苗的有54人,打兩劑的只有22人──看起來打三劑反倒不安全,不過這個數字要經過接種人口比例的標準化(Normalization),才知道疫苗有無保護力;否則以相同的神邏輯,就會推測出「強制騎機車戴安全帽後,高達九成以上車禍死亡的騎士都戴著安全帽,所以機車安全帽殺死更多騎士」的荒謬言論!
根據衛福部疾管署的資料,把接種過三劑及兩劑疫苗的人口比例相減,只接種兩劑的人口約為13.08%。也就是說13.08%的人口比例中該日病死了22人,69.9%的人口比例中病死54人。如果全民都未接種第三劑疫苗,病死人數照比例推估應約為118人(69.9 / 13.08 * 22),而非實際上的54人!從中我們可知,第三劑疫苗確實是有保護力的——單單多接種一劑第三劑疫苗,一天就有63人因而獲救!6月初死亡人數破百後,第三劑疫苗僅僅在一個月內至少讓上千人免於病死!更甭提從今年5月份疫情蔓延開始,以及第一和第二劑疫苗的較弱但還是保護到的人!如果完全沒有COVID-19疫苗,台灣這幾波COVID-19疫情的總病死人數恐怕要在後面多加一個零吧!?
西方醫學史一向把疫苗的發明歸功於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1749-1823),因為他在1796年5月14日進行了牛痘實驗。他以接種牛痘漿的方法,用一把清潔的刺胳針在一名八歲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的兩隻胳膊上,劃了幾道傷口,然後替他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男孩染上牛痘後,六星期內康復。之後詹納再替男孩接種天花,結果男孩完全沒有受感染,顯示牛痘能令人對天花產生免疫。詹納因此被後世稱為「免疫學之父」(Father of Immunology)。
其實,中國古代為預防天花傳染病,早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辦法。種痘的辦法,是採用天花病人的結痂和膿汁,接種到健康人的身上。讓人感染輕微的天花。輕微發病之後,即可獲得免疫力,之後便不會再犯天花。據俞正燮《癸巳存稿》所記:「康熙時俄羅斯遣人到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
不少致命傳染病先後在大規模接種疫苗之下節節敗退,其中包括天花、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症)和麻疹。天花病毒四十年前確定從地球上根除,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種被消滅的致命傳染。天花在1980年被消滅後,全球皆停止接種天花疫苗,台灣1979年起停止接種,該年以後出生的民眾皆未接種。雖然全民不再接種天花疫苗了,第三代天花疫苗對於預防現在在全球多處出現的猴痘仍是有效的。
俗稱小兒麻痺症的脊髓灰質炎,是一種兒童急性傳染病,病毒主要透過糞口傳播進入消化系統,侵入血液、神經系統,然後開始攻擊脊髓,大多數人可以自行復原,但少數的人會造成終生殘疾,最常見的是腿瘸。小兒麻痺症在我們父母輩的時代,還是常見的傳染病,現在在我們的社會中近乎絕跡。
還有,麻疹疫苗在1963年問世,但現在每年全世界仍有約十四萬人死於麻疹。疫苗出現之前全球每年約有兩百六十多萬人被麻疹奪去性命。美國和歐洲近年來麻疹感染病例呈上升趨勢,因為疫苗接種人數越來越少,主要原因是人們擔心疫苗可能會帶來如自閉症等副作用,雖然這方面並沒有確鑿的醫學證據。麻疹主要透過咳嗽、打噴嚏時釋放到唾液細沫中的病毒或直接接觸傳染,症狀包括高燒、咳嗽、鼻炎、紅色斑丘疹,還可引發多種可能致命的併發症,如肺炎、腦炎和腹瀉等等。
西方先進國家愈來愈低的麻疹疫苗接種率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英國前醫師安德魯.維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所賜,他曾任職於倫敦皇家慈善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在1998年撰寫的〈兒童所患非正常淋巴結節增生、非正常結腸炎和流行性腸道發展混亂〉論文中,做出「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MMR)導致自閉症」的結論。該論文後來被發現造假,2010年遭刊登的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撤下。該論文有十三位作者,其中有十位作者在該期刊上發表了向公眾致歉聲明。他本人亦因為多項職業操守問題而在2011年被英國當局吊銷醫生執照。
真實的故事,有時候往往比虛構的更扯,維克菲爾德這名偏執的英國醫師,後來移民美國德州繼續騙吃騙喝。相信他的民眾成立了反對接種疫苗的團體,在世界各地散布不實訊息,讓美國、日本及歐洲近年的麻疹死灰復燃。其中,光是英國官方統計,英國麻疹發病率,近十年即增加了二十倍。這整個事件最完整的報導就是這本《反疫苗戰爭:一個野心勃勃的醫生,一篇只有12位個案的偽科學論文,如何欺騙了全世界?讓英國人付出了一整個世代的慘痛代價!》(THE DOCTOR WHO FOOLED THE WORLD: Science, Deception, and the War on Vaccines)了吧?
《反疫苗戰爭》一開始的重點只有一個人跟一種疫苗。書中主角維克菲爾德是九零年代第一批把MMR疫苗與自閉症聯繫起來的論文幕後推手。他在行醫初期就對克隆氏症(一種炎症性腸病)的病因產生了興趣,試圖把麻疹病毒和這種腸炎聯繫在一起,後來一再先射箭再畫靶。《反疫苗戰爭》講述了讓維克菲爾德臭名昭著的每一個事件,以及他是如何從神壇中跌落下來的。老實說,我個人認為,書中揭示出維克菲爾德及周遭的同伙方方面面的個人資訊,其實是鉅細靡遺到有點超過的地步。
《反疫苗戰爭》作者布萊恩.迪爾(Brian Deer),是一位多次獲獎的調查記者,他於2003年9月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例行指派任務後,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調查此事,超過十五年來用了超過六千份文件和紀錄支持其報導內容,書中註腳就有兩千個資料來源。他為此推出十餘則艱難的新聞報導、一小時的電視專訪、在頂尖醫學期刊發表五篇系列文章,揭露出這個「可能是過去一百年造成最大傷害的醫學騙局」。
維克菲爾德等人和反疫苗團體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迪爾也遭受到他們無情的言論攻擊、辱罵、威脅以及訴訟,在書中他對這幫人也帶著相當強烈的情緒,甚至迪爾自己也成了故事的重要部分,雖然有不夠客觀之嫌,但對讀者來說卻可能充滿戲劇張力。
維克菲爾德最大的問題是他太急著想要成名,一直試圖子虛烏有地尋找不存在病患腸道的麻疹病毒。在實驗過程中,完全沒有考慮控制組和隨機採樣的問題,並且選用了準確度較低的實驗方法。他找到有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參與針對生產MMR疫苗的製藥公司進行集體訴訟,後來被揭露出背後的利益衝突。愈來愈多實驗室無法再現維克菲爾德的實驗,科學界要求他們改用精準度更高的PCR檢測法,以及提供更多原始資料時,他們只是反控遭到不公的迫害等等。
兒童自閉症和MMR的關聯,更像是巧合多過有因果關係,因為兒童能夠診斷出自閉症的時間點剛好是MMR疫苗接種之時。在去除了基於汞的防腐劑硫柳汞(據稱是MMR疫苗的有害成份)後,自閉症仍繼續出現在接種疫苗的兒童中。原本維克菲爾德只是鎖定MMR疫苗,可是當他逐漸被捉包出研究能力不足及論文資料問題重重而被逐出醫界後,反疫苗團體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把他的遭遇描述成陰謀論,然後把所有疫苗描繪成惡魔。
自從維克菲爾德發表了那篇論文以來,生物醫學界對實驗品質的要求和論文審查的嚴格,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然而,因成名或私利的私心而導致公共利益受損的害群之馬再所難免,《反疫苗戰爭》提供了詳實的報導讓我們能夠在試錯中學習,值得關心醫學政策的朋友們好好一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也必須瞭解到為何有些民眾寧死都不肯接種疫苗,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疫苗政策以保護更多的人!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隔離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我兩年多前在台灣登記結婚,可是迄今在馬來西亞仍是單身,拜該死的疫情所賜,對跨國旅行所需的長時間隔離生畏,無法方便地帶老婆回馬登記結婚,也不知道還有多少張罰單待繳。
台灣和一些嚴守國門的國家,2020年相對平穩,在全球許多國家哀鴻遍野時,仍然能夠歌舞昇平好一陣子。可是以為安全,才因為超低疫苗接種率而在去年中陷入愁雲慘霧,仍靠民眾自律儘量宅在家保持社交距離,以及繼續嚴守國門度過。現在遇到傳染力特強的大魔王Omicron變種,才被迫開始轉為與病毒共存。相較之下,對岸只能在國產疫苗保護力不佳又不願承認的情況下,騎虎難下地讓上海封城(或稱「全城靜態管理」),和當初武漢封城被讚為有擔當和魄力,不可同日而語。
兩年前疫情大流行初期,祭出閉關鎖國政策的國家,當然不會受到歡迎。澳洲甚至有一度連國人都無法入境,惹得民怨四起。世界衛生組織(WHO)當初還不斷呼籲各國不要封鎖邊境並且對某些國家的旅客差別對待,結果反而是不理會的國家受創較小。後來,一旦有新變種出現,發現的國家又成了眾矢之的,遭到其他國家封鎖。
除了國際政治紛爭,長時間的隔離,尤其是過去所需要的「14+7」,讓國際旅行變得即使沒有不可能,也成了寸步難行,畢竟來回加起來在防疫旅館隔離的二十八天,不僅在精神上頗為折騰,費用也頗可觀,這還不提因為航班大受影響的高額機票價格。
避免了跨國旅行,我自己沒有經歷過長時間的隔離,經歷過的親友也一向避談那段形同軟禁的日子,但想像一下,出關時應該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吧?因為這兩年旅行的困難,我就聽說不少無法見到家人而造成的憾事。我大伯今年6月初過世,還好5月份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已解禁隔離等旅遊限制,在國外工作的堂姐、堂哥才能回到他身邊陪伴他度過人生最後的旅程。
「隔離」的英文Quarantine,源自威尼斯文「quarantena」,意思是「四十天」。當時,威尼斯把船舶和人員隔離四十天,作為與鼠疫相關的疾病預防措施。1348年至1359年間,黑死病消滅了大約三成的歐洲人口,以及相當大比例的亞洲人口。1377年的一份文件指出,在進入現代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古代達爾馬提亞的城邦拉古薩)之前,入境者必須在一個行動受限制的地方(最初是附近的島嶼)度過三十天,等待黑死病會不會發作。1448年,威尼斯元老院將等待期延長至四十天,由此產生了這一詞。為期四十天的隔離是應對鼠疫爆發的有效方法。
隔離在歷史上並非僅限制封鎖黑死病及COVID-19,把可能染疫的人和健康的人分開,是自古以來人類處理未知疾病的方式。然而,把大量後來證實為健康的人們隔離,其中的人權和法治問題,並不是非黑即白。這本好書《隔離: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UNTIL PROVEN SAF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就要帶我們面對歷史、政治、社會、科技等等中的隔離。
在英文中,「quarantine」和「isolation」意思不同,前者指在不確定是否染疫的情況下進行的暫時隔離,後者則是避免確診者和外界接觸所進行的隔離。不過,中文似乎把兩者都稱作隔離,《隔離》中文版把前者譯為「隔離」或「檢疫」,後者譯作「隔絕」或「孤立」以示區分。如果是後者,因為確診而需要與健康的人隔絕避免傳染,在還受到良好照護的情況下爭議不大。但還不確定染疫與否就要與世隔絕,或禁止人與人的連結,在經濟、政治和法治上就可能受人非議。很不幸的,COVID-19就是一種還未出現症狀或無症狀就會傳染的疾病,要斬斷傳播鏈,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入境者和接觸者隔離。
《隔離》作者傑夫.馬納夫(Geoff Manaugh)和妮可拉.特莉(Nicola Twilley)是美國作家、部落客,他們為了體驗各種古代的隔離設施,在疫情間也冒死繼續旅遊,為本書的寫作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追尋慈善家、素食主義者和監獄改革倡導人士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的足跡,他於1785年開始調查地中海檢疫站或隔離醫院的人們狀況。
為了親自體驗隔離,霍華德冒死登上一艘被感染的船,幾個月後抵達威尼斯的新檢疫站(Lazzaretto Nuovo),在那裡他被短暫隔離在一個非常髒亂的房間,到處都是害蟲。 霍華德安然無恙地度過了他的隔離期。他後來提出良好的隔離設施所需基本要素,從充足的通風到公共宗教服務和富有同情心的關懷。這些在當時尚不存在。
霍華德的終點站是烏克蘭,在那裡他成功說服了可能感染斑疹傷寒的赫爾松(Kherson)居民,在霍華德本人死於該病前不久,搬到了聶伯河( Dnieper River)上後來被稱為隔離島(Quarantine Island)的地方。
在英國倫敦,他們見識了集郵家丹尼斯.凡德維爾德 (Denis Vandervelde)的精心蒐藏,見證了傳染病大流行期間對郵件進行消毒的百年歷史。可能受污染的信件和包裹被放置在裝有香料和香草的木棺中一周,而其他處理方式包括用醋和煙熏處理,或在鐵柵上炙烤。有些處理方式讓信件變質難以閱讀。儘管蓋上「已處理」的戳記,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件仍會被收件人直接付之一炬,因此遺留下來的,罕見到值得好好珍藏。
隔離也會被濫用。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公權力趁機擴權做有罪推定而非符合法治精神的無罪推定,於是隔離被濫用助長了偏見和種族主義,被國家用來重新劃定有爭議的領土的邊界、被大企業掠奪礦產權,被極右派用來迫害移民。例如,澳洲利用防止疾病的藉口合理化白澳政策;美國也曾利用過公共衛生政策,試圖奪取舊金山華人的房產;在美國南方州,也曾利用防止疫情傳播為由限制黑人和婦女的自由。
隔離並不限於人類,動植物的檢疫其實比人的還常見。《隔離》提到一個特殊的例子是,為了保證我們未來還吃得到巧克力,可可樹常需要數年的隔離。馬納夫和特莉的眼光還突破地表,把觸角延伸到了外太空,探討地球人對外星生命汙染地球的恐懼,甚至不惜讓太空人與科學家們和外星汙染一起同歸於盡;另外,他們也對核汙染如何永久封閉在地下鹽層有詳細的描述,科學家為了不讓後代子孫去翻挖的心思創意,也讓人印象深刻,包括基改製造遇到輻射就會變色的貓咪等等。不過各種嘗試似乎只會讓人更好奇到想要當奪寶奇兵吧?
《隔離》指出,隔離簡直就是焦慮的總和,對疫病和外來者的焦慮轉換成對自由生活喪失的焦慮。瘟疫蔓延時,宗教常常不但可能不是慰藉,反而是群聚感染的大本營。在疫情期間的靈性生活該如何自處?對我而言,疫情影響最顯著的也是需要減少宗教活動,例如避免需要群體進行的禪修活動等。《隔離》中提到,在中世紀的斯普利(Split),在一座俯瞰大海的塔上,牧師可以在那的講壇為被隔離在船上的水手進行露天、遠距離的彌撒。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底特律有牧師用塑膠水槍為信眾噴灑聖水。
COVID-19疫情逐漸退散後,可預期的報復性旅遊和消費,會讓航空旅行和全球貿易量不斷增加,使得病菌和病毒的傳播能力繼續加速。生態環境破壞也讓偏遠的野生動物,滲透到人類居所,產生能夠跨物種傳染的新興致命病原體。 面對未來對人類生命構成巨大威脅的傳染病流行,隔離無論多麼陳舊,仍將是有效的防禦手段之一,用於減緩傳染病傳播,讓我們有足夠時間開發疫苗或治療方法。
我們該如何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檢疫需求呢?《隔離》指出,其中一些檢疫措施,已經在COVID-19的應對中有效運用,例如社交距離、接觸追踪和傳染建模;在隔離場所內,需要更加關注管道網絡、通風系統和廢物處理;政府也需建立起公眾的信任,保證會為那些顧及公共利益而受影響的人們提供財政、法律和醫療支持,並鼓勵更大的個人責任感。
隔離人生沒人想過,這種犠牲小我的方式,是把雙面刃,無法簡單地以存廢論斷,值得在大確診的後疫情時代繼續深究!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